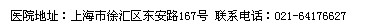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创伤性脑出血 > 脑出血治疗 > 隐形的红字十一
隐形的红字十一
这是第
35篇文章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
隐形的“红字”(十一)
我的父母去世后,村子里的一些人觊觎老父母的宅基地,图谋着要将我赶出村子,理由是我的丈夫是入赘的外乡人,本不属于这里,女儿按规矩不能继承父母的宅基地,因此我必须滚蛋。我本这突如其来的情形击溃了,甚至不能去想为什么,我心里知道,他们是算准了我的父母没有儿子在身边,只我这个寡女实在好欺负,我感到屈辱恐惧和愤怒,我刚把我的老母亲埋葬,尸骨未寒,我几乎连这个破窑洞的小院子也保不住,穷极则凶,我一生忍耐的屈辱和愤怒使我升腾起来,去保卫我的家,保卫我生存的权利,保卫我作为一个女人苟且生存的权利,抢回我不能够被随意摆弄欺凌的最后一丝尊严。邻居是个姓温的凶暴男人,他带领自家的一群儿子气势汹汹地向我的家扑来,为首的他扛着锄头和铁耙子,他们像残暴的动物冲过来,不容分说地扒我的房子,房顶上的砖瓦像雪片一样落下来,刹那间我浑身的汗毛根根竖立,我像一只负伤的母狼,从胸腔爆发一声尖啸,声音凄厉,我不顾一切地扑过去跟他们厮打,不过是活命而已,我不过只是要活下去而已,活下去要经受这样的疼痛羞辱和折磨,这是个什么样的世道。我和我可怜的丈夫在人群中厮打,用鲜血和绝望的暴怒杀出一条活路来,拳头像雨点一样落下,我并不疼痛,我像被泡在寒冬的海水里,脚下有钝钝的刀锋,我在肉体丛林中盲目地捕猎,我用牙齿撕咬,用爪子撕裂触手能及的肉体,在一切胳膊和肚子上留下我愤怒的力量,我可怜的老父母啊,保佑我吧,若我能活过这一回,我那在天上的老父母啊,你看看我。我在人海中机械地抡动手臂,渐渐地我被人们拉开,有一些人将我和丈夫拉到一边,他们劝架,说合,村里的干部也都来了,虽说无用,但毕竟,有人为我说句公道话。
我打完了这一架,突然明白了什么。我真傻,这世道,从来都没有公平,不过是你强我弱,你就可以欺负我。我看看我剩下的人生,从来没有觉得如此的苦涩,也前所未有地坚定。
姓温的畜生依旧每隔一阵子就带着他家的孩子们来闹事儿,他们家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子们都大了,和他们的父亲气势汹汹地站成一排,他家二女儿不善闹事,人长得漂亮,只站在一旁翻白眼,大女儿和小女儿则站在我家墙头,大声不堪地咒骂着,一家大小即刻能把我和丈夫围得严严实实,我气急又毫无办法,要是真打起来,我还能拼命,他们若是这样叫骂而不动手,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凭白地听着他们日复一日地泼着脏水,每日被一帮孩子辱骂着,我真恨自己如此的弱小,才生了一个女儿,又那么小,只会哭,什么用场也派不上!
我这时才知道,我的老父母纵然万般不中用,有他们在,我毕竟还不是孤儿,不会给人这样明目张胆地欺凌。这剩下的人生啊,怎样才能熬过去。要是我也家大业大,有一帮生龙活虎的儿子,那该多好!这充满獠牙的世道啊!
我以为逃过了,却还是失败,那不能承受的命运的刀,终究还是落下来。我不过是个女人。这獠牙般的世界,女人,这两个字像是胸前刀刻的红字,一旦你是女人,你就必须是这种人。你就必须像一块破旧的抹布,替这个肮脏的世界擦掉所有的脏污,你清洁它们,收纳的污浊和痛苦,都是你身上不可原谅的罪孽。
我要是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们,这些孩子们要是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播撒开来,在大地上生根落地,播撒希望,它们像殖民地的统领,将自己的血脉洒遍大平原,占满了整个平原,它们勃勃生机,充满侵略性,充满不可抗拒的力量,它们覆盖了整个平原。它们终将统治这个广阔的平原,它们还将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在平原奔腾的血管中杀出一条火光冲天的路。
我从来不曾想过,这一切都被我的女儿们看在眼里,我甚至完全没有想到,她还存在过。我每一天都奔忙在打仗般的生存战役中,四处起火,我团团转着,惊惶而恼怒,没有人保护我,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怀着最后一个孩子,已经六个多月了,为我做产检的医生们都说是男孩,我骄傲地挺着大肚子,尽管担心,但还是按捺不住地喜悦,这个在我肚子里踢来蹬去的小家伙,他可真结实啊,他是个雄心勃勃的、可爱的、活泼的神的礼物,我每天吃得饱饱的,带着我肚子里的儿子晒太阳,我几乎要哼唱起来。阳光拂过我的脸庞,暖暖的,今年的收成又格外好,黄灿灿的麦子在地里,大地像铺满了金边,微风一过,空气中充满成熟麦田的香味和小溪流水的清脆铃声,我的心像七月的花开,山上的菟丝子开了花,洁白的花和白玉般的藤蔓攀援着,星星点点的喜悦。
一天正午,我在院子里坐着,给快出生的儿子绣肚兜,外面的阳光顺着山峦洒下来,一路为向阳的小径和山脚下的平原铺上明媚的金色,在背阴处,则铺上幽暗的蓝色。山坡上红叶正浓,金色和火红色交织着,五彩斑斓。
突然门被撞开,为首的是镇上计生委的主任,后面跟着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穿中山服的领导们,还有超生稽查组的一个人,他们不容分说将我抬上一个担架,冰凉的金属和奇怪的器械捆住我,我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拼命地挣扎着,叫一旁吓呆了的大女儿赶紧去找她的父亲来,我央求着,求求你,青天老爷,让我保住我的儿子吧。几个人将我抬起来,装上卡车,蒙眼医院,抬进一间手术室,像垃圾一样卸到手术台上,有人在我和我的腰部之间拉起了一道帘子,我看不见自己的下半身,也看不见在帘子那一侧的人们在对我的肚子和我的儿子做什么,我恐怖地叫唤,声音一出口我自己也吓到了,这哪是人的声音,这分明是一头畜生临死前的嚎叫,我终于明白,我是一头活猪。我感到一根针深深刺进我的身体,我想要哭喊,想要推开他们,想要杀掉他们,这群宰猪的畜生啊,我的儿子啊,我的骨血。我渐渐地哭不出来,失去痛感,我能听到金属相碰撞的声音,能听到穿白大褂的人们闲聊的内容,能感到人们撕开我的肚皮,两个人分别向两边拉扯着,一柄刀在子宫上切口,冰凉的一线,液体涌出,机器抽吸的声音,大出血,一个医生冷静地说道,另一个医生说,通知血库。然后有人从我的胸口开始向下一寸寸地按压,孩子太大了,医生说,再使点劲,一寸寸地按压,我听不见孩子的哭声,有什么东西一扯,突然肚子轻了,身体合拢,没有人再扒开我的子宫和肚皮,针线穿过肚皮的声音,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拉紧,再紧一紧,还有一阵灼痛,我的肉体和器官和内脏都摊在这手术台上,所有的一切,我的生命,我的儿子,我的血,我的心脏,肝脏,脾胃,子宫,输卵管,肾脏,大肠小肠,还有宫腔内的鲜血和脐带,还有那个心脏还在跳动的孩子,那团肉球,我所有的一切,我的灵魂,我的肉体,我的未来和希望,这一切,都赤裸裸地摊开在一群陌生的屠夫面前,他们翻检着我的肠子,翻检着子宫,最后检查着出血点,他们拨弄着我的器官,在这冰冷的手术台上,我作为一只正被解剖的活猪,突然觉得这一切都荒谬地变了形。
(待续)
(回复关键词“”可以查看本连载的1--5期。“”可以查看6-10期)
作者简介:
张冬晓,心理治疗师,资深文艺青年。
认真但不严肃,有趣而不活泼。
不包治百病,不卖鸡汤。
心理治疗并非治疗师本人的魔法,而是两个个体在时间的容器内,经过漫长的等待和解密后,惊雷般的相遇。
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