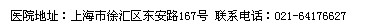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创伤性脑出血 > 脑出血医院 > 狗在江湖
狗在江湖
狗在江湖
1、我爷爷那个年代,长白山下各家养的是那种又傻又笨的土狗,它们都长着狼一样细瘦的身材,没有名字,所有的狗都听得懂同样的召唤的口哨,或者干脆被唤做“狗仔狗仔。”
没有多余的粮食喂狗,它们需要自己谋食。因为常常处于饥饿之中,狗的眼神之中就多了一层卑微。那时候狗还是吃屎的,小孩子撅着屁股在土路旁大便时,手里一定要拎根木棍与狗对峙,狗则吞着馋涎急不可耐地守在孩子身边,孩子一起身,它就会冲过去把一泡屎吃得干干净净。
狗的任务是看家望门,因此夜里它只能住在外面,栖身于鸡窝旁、屋檐下,倘若混上半捆稻草做床就已经是贵族了。好在土狗们并不挑剔环境,生在谁家就把谁当成主人。它们很会苦中做乐,常常跑到土路上追撵嬉戏,为追求母狗而厮咬打架,胜者不知羞耻地在众目睽睽下激情做爱。
倘有陌生人进村,一只狗叫起来,立刻会引来一村子的狗的围观与追撵,倘若这陌生人是个瘦小的叫花子,手里又没有棍棒和石块,这些势力的狗眼就会大放光芒,某一只便会叫嚣着把前爪搭上叫花子的肩膀,张大臭哄哄的狗嘴凶相毕露;另外的狗则撕咬裤腿和衣襟,大声吠叫,把人吓得三魂丢了七魂。
好在那时候狂犬病还没有流行起来,倘若被狗咬伤,流出血来,好心的大婶就会剪下一缕狗毛烧成灰敷在伤口上,这就是治疗恶狗咬伤的灵丹妙药。
尽管狗对人忠心耿耿,人却并不领这份情。倘若急需一顿佳肴来招待客人,主人就会赐给狗一条麻绳在门前的小树上结束它卑贱的狗命。一锅狗肉,再热热地灌下一碗老白干,这是山里人最热诚的待客方式。
长白山的冬天大约要持续半年之久,大雪封山,正是打狍子的最好季节。庄稼汉一到冬天就成了猎手,没事就背上“老洋炮”,穿上羊皮袄,戴上狗皮帽子,领着自家的狗去山上转悠。我爷爷当初养了两只黄狗——大黄和小黄。有一天傍晚,爷爷从山上转回来,偷偷和我父亲说,东山上来了两只狍子,早点睡觉,明天起早去打狍子。说的时候两只狗正懒洋洋地趴在屋地上。
第二天,父子俩早早穿戴整齐,背上老洋炮准备出发,可是两条狗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爷爷气得不断咒骂,正在这时,小黄出现了:狗毛零乱,狗脸上全是血。它见了爷爷就跑过来咬住爷爷的裤腿,爷爷吓了一跳,小黄不管这些,咬着爷爷的裤腿拼命往外拽,爷爷莫名其妙,身不由己地跟着小黄出了家门,见小黄奔的是东山,父子俩似乎明白了什么。后来,小黄松了口在前面跑,父子俩紧紧地跟着,到了一片密林深处,只见大黄也是满脸的血,连狗毛都染红了,一张嘴死死地掐住那只比小牛犊还要大的狍子,那家伙还在挣扎,雪地上星星点点的殷红,真不知道这两只看起来又蠢又笨的狗怎么会听得懂父子俩的话,又怎么会抓住这样大一只狍子。
父子俩没费多少力气就把又肥又壮的公狍扛回了家,邻里羡慕,一家人都高兴,两只狗也得了狍子骨头做奖赏。
又过了几天,我爷爷背着老洋炮带着大黄进山转悠。在一片老林里,爷爷发现一棵巨大的枯树洞口布满了白霜,有着多年狩猎经验的爷爷兴奋起来:他遇见了一头正在冬眠的熊。
爷爷首先要敲树干把熊从冬眠的树洞里叫起来,这叫“叫仓”,等熊懵懂地爬出树洞,稳稳地给它来上一枪就搞定了,能猎上一头熊收获可就大了,而且也是一种荣耀。
爷爷一边想着他的美好愿景,一边嘭嘭嘭地敲着树洞,谁曾想那是只一点也不含糊的熊,爷爷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熊已经向爷爷扑过来了,这个庞然大物欺身爷爷近旁,扬起巨大的熊掌,要是被搧上一巴掌,非得被搧掉半个脑壳不可。爷爷实在无暇转过身来扣动他的老洋炮,慌乱中只闪过一个念头:完了,小命要交代了。
关键时刻大黄冲了过来,它那张嘴咬在皮糙肉厚的熊身上只能算是给熊搔痒痒,好在大黄还算聪明,它一口咬住了熊既没长毛又很脆弱的屁股眼,熊又痛又痒急忙转身,这下爷爷的机会来了,对着熊慌忙扣动扳机。“老洋炮”是一种土枪,用的是枪砂,呈小扇形向外发射。一股猛火射出,熊再无逃脱的机会,被爷爷一枪射杀,可是大黄也没有幸免,枪砂钻进了它的肚皮,顷刻间大黄肚皮撕开,肠子都流了出来,爷爷傻眼了,他扔下那头死去的熊急忙去抱大黄,大黄那个气呀,狗毛蓬松零乱,沾满了血,眼睛血红,目光凶狠哀怨。它拖着瘫痪的下身爬到爷爷跟前拼命地撕咬他,似乎在说,我救了你的命,你怎么能打我呀,这不是忘恩负义么……
爷爷疯了一样把大黄的肠子塞回去,尽管大黄几乎咬断了他的手指,他还是掀开羊皮袄把血淋淋的大黄裹在怀里。大黄不咬了,只发出疼痛的轻轻的呜咽,微闭的狗眼淌出两行混浊的泪来。
大黄被爷爷抱回家,爷爷倾其所能照顾这条半瘫痪的狗,一下子苍老了很多。半年以后,大黄死了,爷爷呵斥了眼巴巴等着吃狗肉的孩子们独自一人把大黄抱到山上,在我家祖坟的附近,爷爷把大黄埋了,那是村里的第一座狗坟。
此后,爷爷不再吃狗肉,每到冬天,爷爷都守在家里叼着他的大烟袋,他老了,不能上山打猎了。
2、我父亲的年代黑狗成为时尚。父亲要来一只纯黑的威武雄壮的公狗,并且给它取名黑虎,不过那只是父亲的一厢情愿,每次叫黑虎它都一脸的茫然,倒是唤“仔仔仔——”时,它才会冲过来,讨好地大摇尾巴。
黑虎和从前的大黄狗们一样,有一条翘翘的、会卷成圆圈的毛茸茸的大尾巴。它仍然挨饿,靠自己谋食,眼光卑微倔强。
那是人民公社时代,私自打猎是被绝对禁止的,况且由于闯关东的人的大量涌入,长白山下人口暴涨,狍子和狗熊也都躲到更深的老林子里去了。想要猎到一头狍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会在天亮之前带上黑虎偷偷出发,倘有人问起父亲的去向,家人总是众口一词说是走亲戚去了,父亲有时会猎到野鸡或是野兔改善一下贫苦的生活。
清汤寡水的日子里,肉的香味最能刺激人们脆弱的神经,那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多疑的邻居早就开始盯着父亲了,当父亲千辛万苦终于捉到了一只瘦弱的狍子,黑夜里在一盏煤油灯下给狍子开膛破肚时,邻居带着生产队长和另外几个人闯了进来。
生产队长叫嚣着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父亲急中生智,说狍子不是他打的,是上山砍柴时黑虎咬死的。父亲一口咬定,黑虎也不做辩驳,只呲着狗牙凶巴巴不客气地望着队长,队长没什么话好说,只没收了一大部分狍子肉扬长而去。
不曾想这回的谎言却给黑虎种下了祸根。
有一天,父亲正准备带黑虎进山,生产队长气势汹汹地带了几个人冲进来,说黑虎咬死了生产队的羊。
告发的仍然是那个与父亲不睦的邻居,说是他亲眼所见。仔细检查,黑虎的嘴巴上似乎确有血迹,狗怒目而视没做任何解释,似乎已默认了,父亲也给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黑虎的清白,况且黑虎是有前科的——它曾经咬死过一头野性十足的狍子呢,这个有力的证据让父亲哑口无言,百口难辩。
父亲忍气吞声说尽了好话,队长才答应对黑虎的死刑可以缓期执行,前提是父亲要把黑虎用绳子拴起来,看好。
父亲找了条足够结实的麻绳,在狗脖子上反复比量,费了好大的劲才做成绳套牢牢地套在狗脖子上,绳套边上又系了一根麻绳,就这样把黑虎拴在院子里的木桩上。
那个年代,狗既不用拴着,也不用牵着。人和狗的相互忠诚完全可以通过话语或是呼唤来维系。黑虎被拴上了,邻家的狗们全都跑过来,有的是看笑话的,有的来做安慰,这些都严重地伤害了黑虎的自尊心,它时而挣扎,时而围木桩转来转去,时而撕咬麻绳,不时焦躁不安地吠叫,对被拴绑被囚禁的现状表示出极大的不满。
还没有拴上两天,黑虎就咬断麻绳跑了,说来也巧,那晚,生产队的羊又被咬死了一只,羊圈里鲜血淋漓。
黑虎不在家,望着咬碎的麻绳父亲只有长叹的份。队长气红了眼睛,背上老洋炮带了几个男人四处去找黑虎。父亲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也跟着这群人四处寻觅。
找到黑虎的时候,它瘸着腿,脚步蹒跚,嘴角和脸上全是血,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队长一行人,并且软绵绵地叫了两声,回头向身后望了一下。队长见了满身是血的黑虎就气不打一处来,举起枪对父亲说,看你家的狗做的好事!羊血还在它身上呢,今天能吃羊,保不准哪天还要吃人呢,这条野狗,我让你嚣张……队长说着就扣动了扳机,黑虎立刻血肉模糊地倒了下去。
父亲冲过去,在黑虎的身边,父亲头皮一炸停下了脚步——离黑虎不远的地方,卧着一头血淋淋的受了重伤的狼。
父亲泪眼模糊,一把揪住队长的衣领把他拽到那头狼跟前。队长哑口无言,所有来追撵黑虎的人全都没了声音。
父亲抱着血肉模糊的黑虎下山,眼泪一滴一滴打在这个哑巴畜生的身上。
3、近年来,乡村里身微命贱的土狗不知不觉绝了种。城里,似乎每一只狗都出身高贵,它们都有好听的名字,穿狗服,吃狗粮,脖子上戴着名贵的狗链,亦如贵妇项上明晃晃的项链项圈。
每一天,主人都会陪伴亲爱的狗狗出去散步,给狗狗洗澡,梳理或修剪狗毛,一口一个“儿子”,一口一个“宝贝”地把它们抱在怀里小心呵护着,狗成了贵族,成了娇贵无比的宠物。
如今,“狗改不了吃屎”这句俗语是被彻底颠覆了,狗们挑食,不会看家,不需打猎,不会为异性打架,一切都由人来伺候,它们只过金丝雀一样娇纵的生活。如果狗的世界有天堂,那么爷爷的大黄和父亲的黑虎也该在谁的怀抱里撒娇罢?
我不养狗,但为狗的命运感到欣慰,在这个丰饶富庶的时代,狗只要学会讨人欢心,学会撒娇就好了。我相信在这个繁华盛世,再也不会看见狗的眼泪。
邂逅了那一车的狗,我没有半点心理准备。那天中午,七月的阳光白花花地射得人眼晕身软,我和朋友约好在一家冷饮店见面。就在那家冷饮店的门口,一辆粗陋的货车,车厢细细密密地焊了些铁栏杆,像一座樊笼停在那里,笼子里挤挤挨挨不知道囚禁了多少条狗,它们全都伸着长长的舌头,炎热和拥挤使得它们仿佛连叫一声的力气也没有了。我仔细看过去,在一些大肉狗的中间,分明有几只瘦小伶仃的宠物狗,它们本该雪白的毛肮脏地打着卷纠结着,目光疲惫,奄奄一息。真不敢相信,它们也曾是某个人怀抱里精心呵护过的心肝宝贝。
下意识地喝了口矿泉水,我发现有两只狗的眼里放出光来,这么热的天,这些狗在太阳底下不知暴晒了多久。我要了一只破碗,倒了一点水给狗们递过去,那只抢到前头的狗贪婪地舔着水,然后,另外的狗挤过来,我的心在狗们舔吮清水的声音里一次又一次地收紧,热泪盈眶。
彪悍的司机吃完冷饮心满意足地上了车,车子发动,猖狂地咆哮起来,我把所有的水倒在碗里放到那些可怜的狗们的车厢,这时,我分明看见好几只狗对着我流出泪来,那苍白混浊的泪一如即将枯竭的生命的泉,在我的泪眼里渐行渐远。
司机说了,要赶去另外的城市,把这批狗送去狗肉馆。
“这鬼天气,狗都热得掉秤了,又要损失好多钱。”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