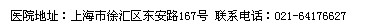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创伤性脑出血 > 脑出血医院 > 诗意文心徐敬亚被困大森林
诗意文心徐敬亚被困大森林
被困大森林
在北中国寒冷的额头上,黑龙江环抱着一片近10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它的范围大约与一个半江苏省的面积相当。大、小兴安岭两条浑圆的山系,像一个巨写在黑土地上的“八”字,为中国保留着一片极为珍贵的绿色。
我很早就知道它的一系列数字,但是我无法体验这些数字后边代表着的博大。我也曾无数次地在纸笔上使用过“博大”这两个汉字,但是现在写出这些笔划的时候,我感到的只恐惧……我的心再次被它征服。确切地说,我是带着一种动物般的瑟瑟之抖!
把一个人全身的皮毛铺开,我们每个人类躯体的面积,不过两、三平方米。如果把这几平方的小面积扔进10万平方公里的茫茫森林中去,你就是枯叶中最小、最可怜的一片。
年8月,在大兴安岭之林,有我一生中最广阔,也最无路的一天。
一种焦灼,突然占据了我
那几天,我一定是中了邪!
我不明白,我深处的焦灼怎样一点点涌出来。是一种未竟的期盼?是多年的野性在安逸中的内乱?还是那股与大森林不和谐的、唯唯喏喏的胭脂气从内部击中了我?
8月11日,在哈尔滨看完了萧红故居,黄昏中,便被朋友的小车送上了去加格达奇的火车。火车是旅游型的,车上的装饰,充满了本时代造作的豪华。火车开了整整一夜才穿过了大庆油田的荒原,清晨的车窗中便出现了大兴安岭绿油油的乔木。我的名字,被写在一块木牌上,在五、六点钟的晨风中晃动。报社的朋友早已在等候。我们全家被装进专车,又被专车送进了地区最顶级的宾馆。我不知道自己忽然得到了什么福份,早餐晚宴,逛森林,游市区,又躯车百余里去看了鲜卑族祖先年前居住的巨大的“嘎仙洞”。
离开加格达奇时,我们被优先送上了软卧。又经过整整一个白天的行程,便到了中国最北的漠河县城。在那里,同样有一个吉普车在等待。在县委宾馆,在漠河乡政府招待所,主人给予的接待,令人受宠若惊。我北方之行的开端,充满了令人不安的伪贵族气息。
全家出门,我渴望得到朋友局部性的接待。但我突然发现,我并不全懂得中国!我不懂得她接人待物的方式,不懂得北中国式的热忱含义。那些天,我诚惶诚恐,内心为之汗颜不止。大概正是在那些时候,我的心中涌出了焦灼的粘液。
离开水泥森林的深圳,进入辽阔北方,我像一个渴望拼命奔跑、渴望拼命淘气的孩子,却被热情而客气地迎进了地毡与美食之中,我乖乖地按照大人们指好的路线,像一个三好学生一样参观着祖国的大好山河。
几天后,我心中的密谋终于成立!
主人客气地把我们一家送上了车厢。妻儿将返南方,而我将中途下车开始只身旅行。深知我心的王小妮临行前说了三个字:别太疯!
又是黄昏,火车从漠河开出。夜里三点多钟,它停在了塔河车站。四周一团漆黑。我像一个拒不听从发令枪的违例奔路者,像一个匆匆逃出客厅的野客,连一分钟也没停地登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
在茫茫夜色中,无论前方是哪儿。无论黑龙江,无论呼玛,无论黑河。
任何前方,都是我的目的地!
五元钱,使双腿得到休息
平民,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自由。
破旧的私人中巴,颠簸在没有柏油的山路上。身边是一个扎着一条深红围巾的农村妇女。车上一股浓重的乡间味道。然而,我竟在那颠簸的气味中睡去。
8月16日天亮时,我醒来。中巴停在一个叫做“十八站”的地方。那里当年曾是慈禧太后派人淘金、运金的第十八个驿站。我饿了,坐累了。我也喜欢这个带数字的地名。我想下车。
我想下车,我就下了车。我是一个自由的旅客。我没有被限定的时间,我甚至没有固定的终点。
正是清早,路边的红砖小店还关着门。拍一拍,便走出来一个没睡醒的老大妈。二两烧酒刚刚摆上,门口便来了骑单车卖山狍子肉的猎户。老大妈为买与不买狍子肉而犹豫,我就说老大妈你买吧。你就给我随便割下来一块,给你10块钱,我下酒。老大妈用40块钱买了整整一只狍子的大腿,她只切下来20-30分之一的腿就给我端上了满满一盘红彤彤的野肉。她给我唠叨她的老头是林业局的副处长,她的儿子林学院毕业后在家里干个体,她还指给我院子里的一辆自家拖拉机。我边喝酒,边像微服察访的官员一样,像模像样地听着这东北的“民情”。
淘金!我突然听到了她说。我一下子站起来。
是那两个神秘的字,触动了我猎奇的神经:远吗?我急着问。
她说很可惜,昨天山上还下来了人。上山没有车,要走几十里山路。
我也是一个偶尔的享受主义者。我不想走几十里,抹一抹嘴我就出了门。
在那个人烟稠密的村镇,我等了三个小时才上了一辆去呼玛的大客车。
呼玛就呼玛!郭颂的东北民歌不就是唱呼玛河的吗。
从乱糟糟的南方,一头闯入静谧的大森林,我像乘上了一部时光机,追看到了中国两种经济体制结合部的早期状态:道路上跑的,大多数还是国家的公共汽车。我昨晚乘坐的私人中巴,是这里刚刚出现的新生事物。一个司机告诉我。各公共汽车站定时发车,如果后一辆车超过前辆车,便违反规定,罚司机元整。
大兴安岭空旷如野,沿途人烟稀少。平均三、五十里才能见到一个村庄。
我“体察民情”的另一次收获是在一个叫兴华的小站上,汽车在那里停车吃饭。我用一元钱买了一位妇女半罐头瓶叫做“都柿”的野果,我就获得了与她交谈的资格。她带着一丝骄傲说她也不是本地人。她现在还是齐齐哈尔的一名工人。因为厂里效益不好,她便到娘家来临时种地。她说她今年种了5亩小麦,能得0块钱。
黑龙江省太大太大。在它的境内,我用汽车和火车已经走过了三次昼夜。而从十八站到呼玛县城,地图上只标着一条蚯蚓的长度。但是沿着那条小蚯蚓,我在汽车上又经过了近一个白天。其中,我站了足足两个小时。在第三个小时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腿开始发麻。
我从口袋里拿出了5元钱,我把钱塞在一个大约10岁孩子的小黑手里,同时我示意他坐到他爸爸的座位上去。我早已经看懂,这个独占一席小家伙的爸爸是坐在前排座位的一个黑汉子。
塞在孩子手里的钱,使孩子呆了足足几秒钟。他看了我一眼,挪到黑汉子身边耳语,那汉子便把他抱起来放到了自己的膝上。同时,汉子把钱往我的手里推。我用双手阻挡了他的手。之后,就是平静。整个过程谁也没有说话。全车人茫然皆不知。
我当然是“坐着”进了呼玛县城。
三百里,去看淘金
我坐着到达呼玛的时间,是8月17日下午3点钟左右。在公共汽车站,一个胖胖的妇女把我接到她的家中。她家是一个有着30多个床位的小型“招待所”。下了车,我就问她黑龙江。她说离她家只有米。
我要马上去接见我那条黑色的江水!在漠河,我已经会见过它一次。现在它流出了公里来到了呼玛。而我也赶来了。
一个多小时后,我疲惫地归来。我的小小身体已经和它发生了拥抱。那条陌生的、急速的江流,把我像一根枯树枝那样冲荡了几百米。我不敢造次,我一整天都没吃一顿像样的饭菜了。
回到“家”,胖大嫂已经按我的要求做好了东北式的饭菜。吃过了饭,她又给我打来了热腾腾的洗脚水。但是当她说到淘金的时候,我立刻把脱下的袜子重新穿上!
再次听到了“淘金”两个字时,我的心里流过一阵神秘的渴望。说实话,我一直对黄金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感到不解,甚至“憎恨”。黄金,这曾使多少人为之赴汤蹈火、血流成河的怪物,人们如何把它从贫贱的泥沙里淘洗出来呢?我要不顾疲劳地去拜访它!我,正是从那座被人称为“淘金者”之城而来,我看到过太多的焦急和贪婪。
几百里内外,到处都是淘金的船!随你什么地方下车。每天只有一班车,半小时后就发!
我立刻掏出钱,请她为我订后天早晨去黑河的车票。我说,我现在就去看淘金!
明天晚上你回不来的!
如果我没回来,车票就是你的。我边跑边喊。
胖大嫂送我去车站,车都开了她还在朝我嚷:你明晚不回来,我就退了票等你!
事后,我才悲哀地知道,为了那些金子——那些呼玛河中不属于我的金子们,我付出了太大的代价,甚至险些跌下生命的边缘。
汽车沿着大兴安岭的这条金脉,走了近三个小时。天黑的时候,我在一个叫“兴隆”的村子里下了车并在路边的“家庭旅馆”里很幸福地住了一夜。
8月18日清早,我乘森林中每天一班的大公共汽车返回呼玛。我要中途下车。淘金,太具有传奇色彩,我忍受不住它的诱惑。背着包出门时,旅馆的房东在后面喊:你不能下车,下了车你今天就回不来了!
我不会听信的。我见到过太多的汽车,我也中途搭过太多的汽车。中途下车,是我的决定。离金子这么近,我不会晓行夜宿地白白奔波三百余里。中了贵族之邪后,我要看的、求的,就是天地山野中的心惊与肉跳。
一棵树,使你觉得美丽。一片树,使你觉得凉爽。一眼望不到边的森林出现在面前,一种美丽而又凉爽的大壮观,有点令人发傻!
经过了日日夜夜的奔波,我终于来到了亲爱的树们面前。不是乘车一晃而过,而是近在咫尺地贴近。一棵棵树,细高而笔直地站着,一个接一个,没有边际!
公路,像一条细黄的带子,从眼前到脑后地穿过森林。
在茫茫森林的路边,我随着一个年轻的武汉人下了车。他在几里外的一条淘金船上打工。我与他边走边谈,我们聊得很好。但他听说我去看淘金后就忽然停下来,最后不走了。他说,你要去你就自己去。船长不让带任何人上金船!
在兴隆,我曾听房东说过,现在上边对私人淘金查得很严。看着那执意不走的武汉人,我便扔下他一个人朝前走。这时,公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周围响着林声。我忽然感到了一种害怕,回过头去看。他还跟在我的后面,正不紧不慢地走。我心里一横:这湖北佬长得太单薄。他敢!
船长是个中年人,面无表情,的确像一个闯荡江湖者。在河边,我以居高临下的表情对那个船长说:我从省里来,我要来看一看淘金。我看的是技术过程。我特地在“技术过程”四个字上加了重音。他,似乎在用心地想着,一面用眼睛细细打量着我。之后,他向停在河心的船招了招手,那条大约有三千吨的大型淘金船真的朝我开过来了。我为我的表情和口气感到自豪。船长说:我有事,失陪。
我扔了半包进口香烟给一群工人。一个瘦长个子就被大家笑着从人群里推了出来。他领我上下三层地参观了几乎整条船。在问过了全部的淘金细节后,我举起相机,对全部淘金过程和船上的淘金机械进行了拍照。这时,他的脸色出现了一层恐惧。
猜得出,让人恐惧的,正是金子。
而我,只是一个从小就对淘金感兴趣的人,只是一个爱按快门的旅行者。但是,我看见得太多了!瘦长人的心里一定在后悔:他不该告诉我这个带了相机的人,这条大船一天可以淘洗几千立方的河砂。经“摇床”过滤后,那几千立方砂砾中会闪现出被视为珍贵金属的细沫儿--每天这条船可以淘出10多两黄金!他更不该告诉我,他的老板一年可以赚到万元以上!
一个人,在天地之间
我一个人,走在黄砂公路上。
几百米以内,一个人也没有。应该说几公里以内,几十公里以内没有人烟。只有我,行进在森林的一条细细的肠子里,向着遥远的呼玛,向着一张属于我的、明天早晨去黑河的车票。
我终于相信了房东的话。
出了淘金船登上公路,我开始等待搭顺风车。但是我很快失望。在半个小时里,我只见到了一辆迎面而来的车。我当然不能返回,我不愿被那个房东嘲笑。
年8月18日上午10点多的阳光,洒满了浓绿的林木,鼻子里充斥着幽幽的清香。我跨着大步朝前走,似乎这条路只属于我,整个的森林都属于我。坐在路边着等待,那不是我的性格。而且,我是一个对什么都感兴趣的旅游者。背起包,沿着公路,我走得脚步轻盈。
路边传来蝈蝈的叫声。它叫得很响亮。我下了公路去找它,我要会见一下此刻与我同处一片森林的小动物。
拨开草叶,我看见了它正在震动中的翅膀。它的身体绿中带着铁色,它几乎透明。我的儿子在漠河就一直想捉一只大兴安岭的蝈蝈。现在,它就在眼前。但是我没可能把它带到几千里外的深圳。我决定对它进行拍照。扑了几次,我抓到了它。
我把它放到了干净如扫的公路上。我必须躲开草丛中杂乱的背景,我要拍一张纯净的、如同褪了底似的昆虫照片。这时,我眼睛的余光发现了一个人!
他,正迎着我,从公路的另一端走来。空空荡荡的林中公路上,他显得十分醒目。我必须重视这个人!这里,不是并肩接踵的都市。一个像我一样的生物,正向我一步步靠近……他高大、健壮,超过任何一头森林中的野兽。
再一次出现的恐惧,使我明白了我目前的处境。我仍在拍照,但心里却在想着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很快收拾好了相机,我决定以漫不经心的姿态迎上去。我也只能迎上去。
从服装上看,他是一个工人。他的手上什么也没有。但是他似乎一直在盯着我,他是在盯着我的那只包和我的高级相机吗?越来越近时,我的心在跳。在两个躯体交错的一瞬,我感到了天地间出现了晕眩与凝固……我们的眼睛相对了,他扫过我的目光极快。我敢说,这时他掏出刀大喊一声,我马上会撒腿便跑。但是我们都没出声。走过了十几米,我回头看,他也正在回头。我想,这时如果我追过去,他也会吓得立刻飞奔。
我明白了,我现在只是森林中的一只随时可能被抓获的“蝈蝈”。
我把双手捂在两耳边,这是我小时从书中学会的苏联边防军在森林里谛听越境者的办法。两只手扩大了你的耳廓,它可以使你在森林中的听力加大几乎一倍。我终于听到了有汽车的引擎声从远处传来。那是在我看完淘金的近一个小时之后。
它一点点地近了。我提前几十米扬起了我的手。我的手挥动着,手的里面预先地充满了感激之情。但是对于汽车来说,它只是一个路边的姿势,甚至只是一种特殊的行乞方式。它一点也没有犹豫地从我眼前飞过去。
没有——丝毫——犹豫!
一片突然翻滚起的灰尘,算是它对我的全部回答。
百思不解之后,终于,我发现了自己的过错:汽车是高速驰来,而我的位置正处在一个漫长下坡的边缘。它怎么可能在下坡的时候为一个路人而刹车?!我在内心里原谅了那位司机,我要找一个最佳的位置。搭车的人要为别人着想,幸福才可能降临。
走过了一个小山梁,它的坡度太小,我感到不理想。
在第二个山梁快要接近山顶的地方,我停下来。我知道,汽车在这里只能使用二档。这样的速度,甚至可以使我与司机之间能有几句求情般的对话。
这时,我感到肚子在响。我忽然想到,从清晨至下午我还吃没一点东西!我有些慌乱地打开包。里面只有两块在哈尔滨吃剩下的奶糖,还有在路上买齐齐哈尔女人的一点点“都柿”野果。
下午,吃了一丛蘑菇
高高的山梁,托起了我。我俯看着大兴安岭。
四面望去,起起伏伏的山脉像刺猬一样密麻地布满了树木。一个人的视野,可以达到方圆几十公里。而几十公里的森林只是大兴安岭一个小小的皱折。现在,这小小的皱折带给我的不再是壮观,而是死囚观察无边牢房的惆怅。
我精心设计的计划再次失败。从上午11点至下午2点,3个小时中大约开过五、六辆大大小小的汽车,却没有一辆车为我停下来。每当远处有汽车声传来,我都郑重地停下来远望着它。在它离我几十米距离时,我的脸上已提前做出了紧张而热情的表情。我有分寸地举起手,有分寸地挥动。我身体前倾着迎上去,我的脸上带着笑--但是,它毫无情义地从我面前冲过去,一点犹豫也没有,一次也没有。它无情地掠过我,就像掠过一个普普通通的木桩。
我不明白大兴安岭怎么了?它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它是淳朴的呀。好客的胖大嫂,热心的房东,给了我座位又把钱向我推来的粗糙的手……我不是一个拦路抢劫者,我的衣着举止百分之百地像一个正人君子。它只要踩一下刹车,只要停几秒钟。几秒钟的时间,不会影响它准时到达目的地。它的里面不是没有多余的面积,我小小的身体对于它的发动机来说就像多载一只蚊子。
但是,辽阔、慷慨的大兴安岭,它没有一点犹豫,它绝不怜悯!
我知道森林的可怕。在加格达奇,当地朋友告诉我,有一年冬天,两个森林普察队员在林子里迷失了整整一个星期。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两个人抱着,冻死在一棵大树下。悲哀的是,他们冻死的地方,离公路只有几里路……有一年夏天,在漠河的林场里,一对恋人随队上山。女人去解手,出来时她跑了几步去追队伍。她的悲剧发生了:那女人不知道,她恰恰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人们再也没能见到她……
我,并没有迷路。路,非常平坦地在我的脚下延伸。
浓绿而多汁的大森林,带着一种绝情的冷酷站在路的两边。我,一个森林的闯入者,一个找不到归路的外乡人,被它团团包围着。在那几辆狠心的汽车掠过我之前,我还在心里滚热地爱着大兴安岭,还在浓汁浓味地欣赏着它的美景。渐渐地,我开始学会了恨。它,无情无义,它置我的存在而不顾。它空有美丽!像一个狠心的女人……
现在,我只是想快一点逃离。
每一次拦车的失败都使我分外气愤。每一次,我都转过身拔腿便走。我忍受不了在路边苦苦等待的焦灼。走!只要还活着,只要还能走得动,呼玛就会越来越近。每一次失败后,我都在一气之下后愤然上路,一口气走出几华里!
下午3、4点钟的阳光照得我满身是汗。从上午10点多开始,我已经断断续续地沿着公路走了几个小时,足足走出了四、五十华里。
再次听到汽车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的内心里忍不住又泛起一种强烈的愿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激动。我再次把我的包收拾好,再次准备好应有的表情和姿势。
汽车是从相反方向开过来的。在此之前,我曾为自己定过一个类似红头文件的规定:凡是相反方向的汽车一律不拦!我不想放弃呼玛县城里的那张汽车票,我还梦想乘明天早晨的汽车去黑河。
那是一台解放牌汽车。我迎着它挥起了手。我的脸上带着最诚挚的笑容,我边跑边高喊着“你好!朋友!你好!”。在一闪之中,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个司机,他的旁边还坐着一个女人。
一片突然涌起的烟尘,一片山野砂土的灰浪,在我眼前翻卷。望着它弃我远去的背影,我大声地唾骂:“狗!”“狗!”
“狗”的狠心令人生恨,“狗”的速度却令人羡慕。只有它才能驾驭这博大的森林。它的里面装满了可爱的汽油,它用机械旋转,它的轮子生风,它像飞船在宇宙中飞驰,它忽略我像忽略一片树叶。
而且,我的肚子里没有汽油,我在挨着饥饿,我已经苦苦走了五、六个小时。
书使我知道森林的里面生长着善良,它的胸怀里养着无数的生物。为了可怜的胃,我走下公路,钻进林子。我不敢走远,我小心地与路平行地走。我像一头饿狼,寻找一切可以吃进去的东西。
我必须尽快找到某种物质,然后把它放入我的胃中。有了力气,我才能走路。
一群小伞在大树下乘凉,我轻轻地托起了它们。那是一组高高低低的年轻兄弟,颜色灰白,精细的小折皱里含着水灵灵的潮湿。据说毒菇都有着美丽的颜色,所以我相信它们是友好的。虽然很饿,我仍然很小心,吃了一个小伞顶之后,我用左手持蘑,右手举起相机,为伞群拍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
我拿起那无价的菌类,把一大颗放进了嘴里。我要采取停食观望的办法,如果半小时后我仍然安全无恙,我才真正获得了吃掉全部的资格。
蘑菇的出现,使我重新恢复了旅游的兴致。我看见,森林的边缘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有一种小蓝花,像吊钟。有一种粉红花像串状的剑兰。十几分钟内,我就采了满怀抱的花。
远处,闪出一片醒目的黄色。我穿过树林,看到一丛大约一平方米面积的特大花群。它的叶子像南方的芋头,每一株上都开着一串黄花,筷子那么长,乒乓球那么粗。我站在它的面前,心中感到一丝空旷。在这无人的森林中,没人和我一起欣赏。
半小时后,我吃掉了全部的蘑菇。我感到很高兴,我没有晕倒!
这时我发现了榛子。我是20多年认识它们的。我当年插队的山上,每到秋天,榛柴稞子上都果实累累。但是现在,我像一个刚下了飞机的贵宾,怀抱里满是鲜花。在榛子和花之间,我要作出选择。
我找到一片规整的森林作背景,我把全部的野花一棵棵插进土里。我要“伪造”一片森林中自然生长着的鲜花。放弃这些可爱的花朵之前,我要拍一张谁也拍不到的照片:那上面开满了世界上最密集的野花。是二、三十支小蘑菇给了我好的心情。在一瞬间,我把它们一片虚假的繁荣全部地装进了我的相机。
我不能捧着满怀的野花,美丽而凄惨地行走。在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里,没有人值得我向它献花。美丽和进食,一点也用不着犹豫。吃,才能使我足够美丽。
正是盛夏,榛子还没有成熟。它的果实被包在一层绿色的衣壳里。我咬了一颗,里面有饱满而多汁的果实,像一个虽未成年的、但已经长到了大人高度的中学生。大自然毕竟是慷慨的,我把衣服脱下来,把两只袖子扎起,抱着满满一包榛子回到公路。我是一个飘泊的鲁滨逊,我的家不在海岛,我的家在一条长长的、没有尽头的四、五米宽的砂石公路上。
四条大汉,恶骂着冲来
现在,我是一个最富有的人。在这个下午,整个大兴安岭森林里的野花、榛子和全部的蘑菇都属于我。我只是没有金子,没有汽车。
我的牙被“年轻的中学生们”咯得发痛。我找到了一块小鹅卵石,在一块更大的石头上敲打它们。像在几万年前荒凉的丛林里,我一声声地敲响整个地球。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新石器时期的原始人,他,正在树下敲击野果。
太阳一点点地偏西。我看了看表,时间已经接近下午6点。
6点,再过一、两个小时,天将变得黑暗!也就是说,整整一天,我没能逃出森林。我只有唯一的救命希望:等待明天早晨8点钟的那一班公共汽车。我恨这闭塞、落后的呼玛,恨主管交通的某一个副县长,恨那些诱惑我下车的金子们……
我的表,嘀嗒地走着。天空正在无情地暗下去。到了夜晚,森林将一团漆黑。我想到了黑熊,想到东北虎……我无处藏身。我连一个小小的山洞也找不到。我曾想到过掘一个猫耳洞。我手里没有任何利器,只有相机上的三角架是金属的。它由三层粗细不同的铝管组成,是我在哈尔滨刚刚用元买下的。它的笔直与圆润,将在大兴安的山石上变得扭曲……如果掘洞,我必须趁天亮时动工。我不会心疼那元,如果没了生命,连相机也将属于别人……
但我终于没有掘那伤心的洞。我不相信我会死无葬身之地,总有一辆车能载着我逃离。我不死心。
又向前走了几华里后,我竟在公路旁发现了一处山泉!
它并不清冽,水里漂浮着落叶,里面悬着一些细碎的草木,里面也一定有很多生物。我顾不得了。我低下头去喝,但是我的嘴够不到它。我发现把嘴降到比脚还低的程度非常非常困难……就在我手捧着喝到了水的时候,几滴血落到了水里。
是我的血。我的鼻子出血啦!
在公路上走了几乎整整一天,又热又累,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点正式的食物。我已破败不堪,我甚至感到了一点点晕眩。但是我很快清醒:徐敬亚,你要挺住!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自我怜悯!绝不能站在自己肉体的立场上。这时,你只能坚信一点:坚信自己生命无比顽强!
我拭去了鼻血。这一点点血算不了什么。它只是鼻子过分干燥的结果,只是头部过分倒悬的结果。我毫不忌讳地大喝了几口泉水。我还用那“血水”洗了脸,洗了头发。最后,我把毛巾沾湿。我要带走并储存一些水份,在我的脸再次干燥时,我还会得到它的一丝湿润。
我已身临绝境,我决定强行登车!
我被迫向大兴安岭宣战!
再次观察地形后,我又在一个非常漫长的上坡路段停下来。我仍然把强行登车的地点选择在了快到山顶时汽车最慢速的位置。我要登的,只能是解放牌载重汽车。它的司机楼旁,有一块铁的踏板。我可以一边呼叫着朋友啊朋友,一边奔跑……然后,我纵身一跃……
前面传来马达声,越来越近。
那不是汽车,它是一辆摩托。整个一天,我没有看到一辆摩托,也没有看到一辆小型轿车。
我举起手,拦它!
现在,我不怕任何人。一整天的孤独与迷走,使我还怕什么?吃了蘑菇,吃了野榛子,喝过血臭泉水的人还怕谁?
摩托放慢了速度,黑而瘦的车主人细细地打量着我,是那种从上到下的、审视的打量。他又飞快地看了一眼我的包。他,竟停了下来。
确切地说,它是一辆生了病的摩托。摩托主人说他从呼玛来,他已经走了一个下午,走走修修,每小时的速度不到20公里。他看着疲惫的我说:这里离呼玛还有华里!
华里呀,你是如此残酷而漫长,你几乎断了我走下去的信心。
我在地上转着,在那辆因我而停的病摩托车旁,我想着可能与它发生的宝贵的关系。正在这时,远方传来了汽车的声音。我果断地说:拦车,你帮我拦车!
他点了点头,把摩托微微靠向了路中心,我张开双臂等待着。我对自己说:我现在是和另一个人在一起,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
是一辆北京吉普,远远地飞腾着灰尘,而且它也恰好是开往呼玛方向。虽然上坡,它的速度仍然飞快。它,显然已经看到了我们。但是它没有一点想减速的迹象。它,越来越近,我已经看得到前排坐着的两个粗壮男人了。
我迎着车没有动。我张着双臂。我大声呼喊:请停一停!请停一停!!
“卡--!”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吉普车猛地停在我前面两米处。我用力地笑着迎上去:“同志,能不能搭一段车,我付钱……同志,”
没等我说完,车上猛然跳下两个汉子,之后是第三个,第四个……脸上很油胖,装束很富贵:找死!你他妈的疯啦!有你这么拦车的吗?!揍他!
他们向我扑来,速度突然。当先的已经亮起了拳头。我飞快地绕向车后,双腿向后退缩着:对不起,对不起,我付钱……对不起……
这时,我听到一阵摩托车的发动。那黑瘦人见势不妙,正驰离而去。
对不起?一个对不起值多少钱!你有钱算个屁,到呼玛要10万,掏钱吧!
他们一边恶骂着,一边向我冲来。我急速地后退,但四条大汉竟追上来,离我只有几米远。我转过身,开始跑。一直向后跑了50多米,没有听到追上来的脚步声音,我才转回身去看。
远处,四条汉子仍在向我这个方向叫骂。他们在用手指点着我,说着什么。我,只能任他们打量着、指点着、骂着。我的心里一片慌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是这样可怜地与他们对峙。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他们追过来,我更快地逃。
他们没有追。他们在撒尿。他们在集体地向着我的这个方向撒尿。这是侮辱!但侮辱不威胁我的生命。我眼看着几十米外的侮辱朝着我发生,然后结束。
过了不到一分钟,他们全都上了车,吉普车马上消失在树的远方,山的远方……像一个从天而降的鬼!
我惊魂未定,我的头脑里忽然一片空白,类似晕倒前的感觉。
我忽然懂得:我怕。我怕大兴安岭,怕一切汽车,怕汽车里的一切人。
入夜,大兴安岭的善良之光
天已经微微的黑了。冷风吹过瑟瑟的树林,吹过荒凉不毛的路面。
我还活着,生命与财产一丝未损。
我不想再向前走哪怕一步。公里是一个致命的数字。我不敢再强行登车。我宁肯迎接黑夜。我为那四个可怕的国人悲哀。我为他们心中的恶意而悲哀。我为这令人发指的黄金之地悲哀。我也为我的孱弱无武而悲哀。大森林,你可以淹没我的身体和经历,却淹没不了我的悲哀。
我坐在路边。我准备一整夜地坐下去。我没有别的办法。我黔驴技穷!
究竟是什么,使朴素、憨厚的大兴安岭变得如此恶毒与凶险?究竟是什么咒语,封锁了这一片无边、高大的善良植物?现在,我像那个瑟瑟发抖不敢引人上船的武汉打工者,像那个害怕拍照的瘦高个子,像逃离而去的摩托……我实在不明白,大兴安岭得了一种什么狠毒的病?
可以说,天已经完全黑了。
森林中出现了涛声。对于我,涛声毫无美感。这是将要淹没我的涛声。这是致人于死地的涛声。
除非出现奇迹,除非天上出现营救的直升飞机。
人类已经进化到了二十世纪之末,世界上出现了无数尖端的科技,而人类本身却没有一点点进化。我的腋下不能生出翅膀,我的灵魂不能向远方的亲人发出任何一点信息……
在轰呜的汽车声中,两道光柱由远而近向我扫来。
我本能地站起来,飞快地站起来!
我仍要挣扎,做最后的一次挣扎。我要逃离这黄金宝地。
在公路的侧面,我奔跑着迎上去。我仍高喊:请停一停,停一停!停一停!
它没有停。那辆解放牌汽车没有停!它拒绝解放我!
我继续挥着手,继续与它同方向并排地奔跑:行-行-好!行-行-好!我已经用了更加可怜的句子:行-行-好!你们行-行-好啊!
是我选择的那条漫长上坡路帮助了我。汽车跑得不快,我奔跑着,我不敢强行登车。我几乎与它同速地跑着。我要拼上全部的力气,只要它不停下来,我死,也要一直跑下去!
行行-好!行行-好!……这已经是纯粹的乞求者的声音和口气。10米、20米,我已经跑出了多米……
忽然,我心里涌上来一股暖流:我发现,车的速度减下来了。行行-好!行行-好!……我用更大的声音高喊着。我害怕这好事会突然失去,我担心它再次突然加速!
终于,车在黑暗中完全停下来了。是我声嘶力竭的叫喊,还是我摇摇晃晃的不懈奔跑感动了他们?整整一天,终于有一辆车为我而停在了路边。
我终于感动了上帝!
我会永远记住那个生了一付好心肠的司机,我会记住驾驶室里的另外两个美丽的女人。我也会记住车厢板上站着的大大小小、全部美丽无比的4个人影。
迎着风,手握着栏杆,我与两个大兴安岭男人和两个10来岁的女孩儿站在一起。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两个女孩站在黑黑、跳荡的车厢板上,而她们那对我如此善良的母亲却安坐在驾驶室?那两个愉快的小女孩儿不断地唱着歌。我至今还记得她们在呼呼风声中伸着小脖颈的神态,她们反复合唱的是《女人与老虎》。在黑色的车风中,我用手臂护着低矮的她们。我要用实际行动感谢我的救命恩人。
我在心中对自己说:这是一车快乐的人,一车穷人,一车与黄金无关的人。而我也是一个穷人。天下穷人,用贫穷串连着没有钱的心。
当汽车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我才懂得华里的份量,我才知道坐在汽车里的人对路面上景物的那种天然的漠视、厌烦,甚至警觉。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加重着我对车主人的感激之情。
在经过了一场寒霜的心里,我为黄昏时的遭遇而阵阵后怕。如果那四条汉子向我追过来,如果他们穷追不舍,不出0米,我无疑将被抓获。如果他们内心中生出更加可怕的恶意……渺无人烟的大森林,可以消灭一切痕迹!如是,警方和我的后人将感谢那弃我而去的摩托人。他,可能成为一次森林凶杀案唯一的目击证人……
年8月18日夜里20点45分,我“站着”,再次回到了呼玛县城。
下了车,我用最深情的口气向司机和全车的人道谢。我把一迭10元人民币塞进车门。我伸出手,向着他们挥动,向着整个大兴安岭全部善良的人们挥动。
第二天,我准时乘上了开往黑河的汽车。前个晚上,已经为我退了车票的、好客的胖大嫂指点了我对大兴安岭的百般迷津:你不该去看淘金。因为金子,林子里已经连续出了几起人命案。有的杀了人之后还劫了汽车。所以,在林子里,再好心的司机也不会停车的!
我,终于明白了一切:杀害了我整整一天安全感的,正是我不远千里探看的、闪闪发光的黄金。
·12·20
作者简介:
徐敬亚:诗人、评论家。年生于长春。海南大学诗学中心教授。著有评论集《崛起的诗群》、散文集《不原谅历史》等。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