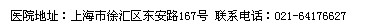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创伤性脑出血 > 脑出血护理 > 出轨后男人身体上会留下这些痕迹,可惜很少
出轨后男人身体上会留下这些痕迹,可惜很少
寂静的深夜,省城某六星级酒店。
这是全省最高档的酒店,顶层的总统套房。
房间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光线很暗。
一对青年男女站在落地窗前,深邃的天穹下,是一派灯火璀璨的城市夜景。
“啪嗒”,男人打燃火机凑近点烟,幽蓝的火苗映着那张年轻的脸孔极是英俊。
“我这辈子横竖是讨不了你欢心了,想你妹妹平平安安在省城念完三年大学,就好好琢磨着该怎样哄我高兴。”他唇边扬起一抹邪恶的笑。
“对不起我不会哄人高兴,你想要什么拿去就是。”女孩说,眼底闪着倔强的光芒。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他一口烟雾喷在她光洁如玉的脸蛋上。
女孩心一横,走到床边开始脱衣服,外套,T恤,短裙……扔了一地。
贴身穿得是一套黑色的调整型内衣,她没有勇气再脱了,直接躺在大床上。
他掐灭烟头走过来,脱掉衬衫西裤扔在地毯上,她下意识阖上眼。
“睁开眼看着我。”他命令说。
“你快点。”她催促。
房间里忽然一片沉寂,她等了很久忍不住睁眼,他站在床边只穿了一条三角底裤,身材是极好的,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在幽暗的灯光下泛着魅惑人的光泽。
“你能不能快点?”她感到难堪。
“我没兴趣和一个木头人上床。”他语带嘲讽,从地毯上捡起她的衣服扔在她身上,“不愿意没人逼迫你,门在那儿,你现在可以滚了。”
她死死咬住嘴唇,过了许久,她问:“有酒吗?”
他盯着她看了数秒,走到酒柜前取出一瓶开启过的洋酒和一个酒杯。刚回到床边,她忽然直起身子一把夺过酒瓶,扬起脖子咕噜噜灌了几大口,“呯”地把酒瓶往床头柜上一掷。
“怎么?想在我面前表演慷慨就义啊?”男人冷笑一声,转身欲走,“我从不和醉酒的女人做,你……”
她忽然扑上去抱住他,用唇堵住他的嘴,吞掉他未说完的话,他怔了几秒钟,马上搂紧她疯狂地回吻她,霸道地侵占她全部的呼吸,两人一起倒在床上。
褪掉她最后的束缚,他撑起身体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声音充塞着沙哑:“是第一次吗?”
“不是。”她听见自己说。
答案早在他意料之中,心里却隐隐失望,犹疑了那么几秒钟,他埋头吻住她……
用这样卑劣的手段强占她,不是他想要的,可如果不这样,他这辈子也许都没有得到她的机会。
他只想要她,把她留在身边,仅此而已……
一年前。
江蒙到海市一年后终于找到霍睿东,两年前给她留下一条手机短信就不告而别的恋人。
就在“青春风采大赛”初赛的比赛现场,她是参赛选手,他是大赛赞助商,她在T台上走秀的时候,他就在观众席前排和一个小美女卿卿我我。
她以最可悲的方式引起了他的注目,故意摔倒在T台上,工作人员扶着她往后台走,她回眸,正对上他错愕震惊的表情。
她笑了。
也就在那一天,她被一起参赛的好姐妹何玉莹设计出卖了,把她当成祭品一样献给一个男人。
那晚何玉莹说她过生日,硬把情绪低落的她拉到了海市最著名的夜总会皇后大道,一走进轩敞豪华的包厢,江蒙就好奇地问:“你订这么大的房间,不会就我们两人吧?”
“哦,我那些朋友晚点到。”何玉莹笑笑说。
刚坐下一会儿,服务员就送来了洋酒,果盘和小食,何玉莹嚷着说无聊,要江蒙陪她玩色盅。
江蒙不太会玩,可她酒量好,也就舍命陪寿星女了。
轩尼诗XO加冰块,入口辛辣,江蒙也不记得喝了多少杯了,她的意识渐渐模糊,何玉莹递给她一杯果汁,体贴地说:“别喝太多酒了,喝杯橙汁。”
是橙汁吗?味道怪怪的,真苦。她仰靠在沙发上,头昏昏沉沉,身体像是着了火一样,越来越热,整个后背都被汗水濡湿了。
包厢里的音乐震耳欲聋,灯光也是暧昧未明,糜烂的气息在空气里弥散。
一个男人走进包厢在她身边坐下,从台面上拿了一杯洋酒放在她唇边,诱哄道:“宝贝,是不是渴了?乖乖喝下去就舒服了。”
她睁大眼努力想把眼前的男人看清楚,意识却一片混沌。
“睿东,是你吗?”她喃喃问。
“宝贝,你想我是谁我就是谁。”男人邪恶地一笑,搂过她的脖子,将酒强行给她灌下,她剧烈咳嗽起来,连带着一阵反胃,捂住嘴想吐。
“宝贝,别吐,忍一忍就好了。”男人拍了拍她的背。
她强压下那股子恶心,心脏如擂鼓般狂跳,,震撼的音乐一声声都像敲打着神经,刺激得她莫名地兴奋,她想呐喊想起舞,四肢却疲沓无力,终是软软地瘫在猩红的沙发靠背上。
男人饶有兴致地瞧着眼前的猎物,伸出手去抚摸她的脸蛋,慢慢落到她的颈脖间,触手是脂玉般的滑腻。
手感真好,看来今晚一定是个销魂蚀骨的夜。
他惬意地眯起眼,喷了口烟雾在那张被酒精晕染成酡红的脸颊上,意识处于混沌状态的她仿若未觉,一双如丝媚眼仿佛含着情,蕴着笑,勾得他欲火直往小腹窜。
他正盘算着是不是就在这儿将她办了,何玉莹推门而入,走过来一手搭在他肩头,媚笑着说:“事儿我给你办了,你准备怎么谢我?”
他将烟头掐灭在烟缸里,反问:“你想我怎么谢你?”
“你说呢?”何玉莹笑得轻佻,又想起什么来,说,“哦,我看到沈斌了,正在二楼挨个儿推包厢门呢,不知道在找谁。”
“你说什么?”他像是火烧屁股一样跳起来,“我得马上走了。”话音未落,人已经冲出包厢了。
“喂,她怎么办?”何玉莹喊了一嗓子,看了一眼沙发上神志不清的江蒙,跺跺脚也走了。
几分钟后,一个年轻男人走了进来,空气里是巴西雪茄特有的醇香,他吸了吸鼻子,冷笑一声:“王八羔子,肯定是闻风跑了。”
他走近沙发看了看江蒙,长得很标致的一个女孩,皮肤白嫩,年纪也很轻,形容却痴痴傻傻,明显是被人下了药。
这崔志浩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又TM玩这种欺男霸女的下三滥勾当,也不怕遭报应。他暗骂一句,转身欲走,走了几步又觉得不对劲,这女孩眉眼瞧着怎么这么熟悉?
走回去又仔细瞅了瞅,一时又想不起来。“今天算你撞大运遇到我了,我就做一回好人吧。”他打横将江蒙抱起离开了包厢。
将神志不清的江蒙放躺到车的车后座,他坐进驾驶位发动了引擎,悍马车很快离开了停车场。
江蒙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身在何处,全然陌生的坏境,厚厚的深色窗帘遮住了整面墙,室内光线暗暗的。
她从床上爬起来,光脚踩在柚木地板上,蓦然发现身上套了一件宽大的男式衬衣,她懵了。
仔细回忆了昨晚的事,隐隐记起自己是喝了何玉莹递过来的一杯橙汁后就感觉不对劲的,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她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醒了?”一个男人的说话声把她吓了一大跳。
她转身,一个年轻男人正站在身后,个子很高很挺拔,狭长的黑眸明亮而有神,浓眉飞扬,很有几分霸气。
这个男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警觉地后退几步,声色俱严:“你是谁?我又为什么会在这儿?”
他心说,昨晚如果不是我到夜总会去逮崔志浩那厮,恐怕你早就被他吃干抹尽了。
见她像只受惊的小动物一样戒备森严,他又感到好笑,有心想逗弄她,便说:“你对昨晚的事真的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吗?你是女人,我是男人,你说我们在一间屋子里能干些什么呢?你没注意你穿的衣服换了吗?”
她一惊,睁大眼恶狠狠地瞪着他,那种眼神似乎恨不得在他身上剜一块肉下来。
“睡过就算熟了,不必把我当成仇人一样吧?”他逼前一步,继续逗她。
她脸都白了,牙齿紧咬住嘴唇,胸脯剧烈起伏着。
“你叫什么名字?万一哪天隔大马路上碰到你,也好有个称呼啊,毕竟……我们……”他坏笑,故意话说一半。
忿恨喷薄而出,她蓦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冲上去一头撞向他的腹部,他猝不及防,一个趔趄向后一栽,四面八叉仰躺在木地板上。
后脑勺被撞得闷痛,等他回过神来,她已经一阵风似地跑了出去。
靠!看来好人还真不能做,死逼丫头,连恩人都要谋害。
心里积了一股怨气,他起身就冲了出去,她刚捣鼓开门锁,正欲拉门,他伸出手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挣不开,回身乱踢乱抓,在他脸上挠出几道血印子。
敢情你是属猫的呀?脸上是火辣辣的痛,他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用力抱起她走到沙发前将她塞了进去,曲起膝盖死死抵住她,身体被他压制住了,她的两只手还在空中乱挥乱舞。
“你放开我!神经病!变态!”她怒叫。
他抓住她的两根胳膊用一只大手握住,另一只手开始解皮带,她大骇,眼睛瞪得像是要滴出血来。
他故意放缓了动作,慢条斯理地解开皮带,唇边浮起玩味的笑意。
“你想干什么?”她颤声问。
“你觉得我想干什么呢?”他笑,用皮带将她的两只手捆在一起,又脱下衬衫绑了她的双腿,“爷就是想让你冷静冷静。”
她紧张的情绪略略舒缓了,身体却还不屈服地扭动着,凌乱的长发拂了满脸,衬衫往上滑,光着两条光洁如玉的大腿,那画面香.艳无比。
他小腹一紧,嘴里却说:“你昨儿嗑了药,像条死鱼一样,我可是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再说了,就你这姿色,海市多了去,随便一抓就一大把。”
她只鄙薄地瞥了他一眼,便阖上眼不再说话,也不再作无谓的反抗了。
在赛场上和他四目相接那一幕不停在脑海里闪现,还有他身边那位温婉可人的女孩,能和他在公众场所出双入对,关系定是非同一般。女朋友?未婚妻?太太?
可是,无论他们是什么关系和我还有关吗?
原以为是可以生死相随的爱,对他来说也许只是个或真心或假意的游戏,我对他来说算什么?对了,他的家在海市,当年常驻江县是为了生意上的事。寂寞时的消遣品?或者是一场时间比较长的艳.遇?
一只略嫌粗粝的手抚上她的右腿,一片清凉,淡淡的薄荷香。她睁开眼,他正拿着一瓶药油倒在手掌上帮她搓捏大腿上那一大块淤青,那是昨天她故意摔倒在T台上时受的伤。
被一个陌生男人这样触碰,感觉很怪异,话说出来自然不会好听:“你把我困在这儿有什么目的就直截了当点,不用假惺惺的装好心。”
大腿猛地一疼,她哼了一声。
他狠捏了一把,还嫌不解气,恶声恶气:“你以为你是谁?天仙啊?你想跟爷睡,也要看我乐意不乐意,要不是看你可怜,早把你扔大街上去了。”
“我昨晚被人下了药,今天醒来就躺在陌生人的床上,你的意思是我还应该感激你?感激你把我绑起来?”江蒙冷笑。
“你刚才和一只张牙舞爪的小野猫有什么区别?我不绑你,好让你在我脸上多抓几道印?碰到你算我倒霉,救了你还讨不了一句好,”他憋屈得紧,手下动作更是重了几分。
江蒙疼得咝咝吸气,狠剜他一眼:“我昨晚人事不省,自是由着你瞎编乱造,你和何玉莹合计着来谋害我,还要在我面前摆出恩人的姿态来,也不嫌恶心?”
“我谋害你?”他气结,“你和我八竿子打不到边,我害你作什么?我想找女人,送上门来的多得是,犯得着费那些闲工夫?你还真把自个儿当回事了。”
她压根儿不信他的话,只觉得那只大手在她大腿上揉捏得越发起劲儿,说不出的暧昧。
“你别再碰我了,我要回家。”她只想离开这个地方。
昨晚帮她换下那套汗湿的衣服时,就看到了她腿上的淤痕,那时已是半夜,他也困了,早上睡醒后就开车到附近的药店里买了药油。他平素也不是什么心慈手软的大善人,只是见到她有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仿佛很久以前就认识似的。
“给我把嘴闭上。”他气她不识抬举,“医院检查,看你哪儿破了没,有证据好打报警把我抓进去。”
见她懵懵的,他说得更白了:“你不是说我谋害你吗?是个雏就检查膜破没,要不是就查查看有没被侵犯过。”
赤裸裸的话让江蒙很是羞愤,真恨不得扇他一个耳光,奈何四肢被绑得紧紧的,只是徒劳地挣扎了几下。
活色生香的美人图,他一个正值青春鼎盛的男人哪儿能淡定?喉头一阵发紧,粗声说:“乱动什么?考验我的定力是不是?我提醒你啊,我可不是柳下惠,把我火惹出来,后果自负。”
“无耻!”江蒙咬牙切齿。
他很是郁闷,活了二十几年,难得做回好人,这死女人非但不领情,还把他当成仇人似的,活脱脱一现代版农夫和蛇的故事。
药油往茶几上一掷,他去浴室洗手,站在洗漱台前,他往镜子里瞅了瞅,不仅脸上好几道血印子,连脖子上都被她的指甲划破了,不就是兴致来了和她玩笑了几句吗?至于吗?天地良心,昨晚帮她换衣服的时候,他可是一丝邪念都没有。
回到客厅,她仍用怨恨的目光瞪着他,他搬了张椅子在她面前坐下。
“崔志浩你认识吗?”他问。
她一怔,下意识点了点头。
“他和我有过节,我昨晚跑到皇后大道去逮他,结果找到他包厢的时候,他人已经溜了,你那时候正躺在沙发上神志不清,我一时发善心就把你救了,事情的经过就这样。”他可不想继续背黑锅了。
她对他的话半信半疑,她是认识崔志浩,可也有好几年没见过面了,昨晚明明是何玉莹带她去皇后大道的,怎么又和崔志浩扯上了关系?
“医院洗胃输液,你一直人事不省,医院后我也不晓得该把你往哪儿送,只好把你带回家了。”他接着说。
她沉默了许久,说:“昨晚的事我不想再追究了,算我交友不慎吃了大亏,现在,我想回家了,请你放了我吧。”
她的语气冷冷的,让他很不是滋味,站起身闷声不响帮她解了绑住手脚的皮带和衬衫。
因为大力挣扎,手脚刚被束缚过的地方有两道勒痕,她淡淡地瞄了一眼,赤脚站在木地板上就往门口走。
“你就这样走出去?”他提醒她,“你昨晚穿的衣服我用洗衣机帮你洗了,我去看看晾干了没有。”
她的脚步停了,不回头也不说话。
去阳台收了她的T恤牛仔裤走回客厅递给她,他装着不经意看了看她手腕和脚踝上的勒痕,心里竟有几分愧疚。
“进房间去换吧,换好了我送你回家。”他说。
“不用了。”她漠然说,人已经转身进了卧室。
换好衣服走出卧室,她看也不看他一眼,径直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天空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雨丝夹带着寒意扑面而来,衣衫单薄的江蒙激灵灵打了个冷颤。
春寒料峭,她的心更是一片荒芜。
两年前,相爱三年的恋人不告而别。
一年前,父亲心脏病发作从复式楼的楼梯上滚落下来,医院当天就停止了呼吸。
她是无神论者,可接二连三的变故让她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产生了畏惧,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命运之手在翻雨覆云。
一辆悍马不紧不慢地跟着她。沈斌吸着香烟,眼睛透过车窗注视着那个羸弱孤单的身影。她前脚刚一离开,他后脚就跟了出去,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他救了她,可反倒像是他亏欠了她什么似的。
她已经冒雨走了大半个小时,雨势渐渐大了,她也似乎浑然不觉,低垂着头,神情凄惶无助。
他一踩油门,冲上去将车打横停在她前面,头伸出车窗招呼她:“上车来我送你。”
她抬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绕过他的车继续往前走。
他推开车门下车,疾走几步拽住她的手臂,说:“你是不是昨晚嗑药嗑傻了?雨这么大在大街上瞎走什么?”
“滚开,别碰我。”她厌恶地说。
“跟我上车,我送你回家。”他用力拖住她,另一只手就去拉车门。
“放开我!”她哪里肯依,挣扎着想要甩掉那只钳制住她的大手,无奈他攥得紧,情急之下,她埋头就去咬。
手背钻心的痛,他倒抽一口冷气,心里怒极,一把将她拦腰抱起往副驾驶位塞,她在他怀里奋力抵抗,嘴里骂道:“你有神经病啊?我不要你管!”
将她按坐在皮椅上,他低着头替她系安全带,她伸手就推他脑袋,身子还在座椅上不屈服地扭动。
他双手按住她的肩膀,冲她大吼:“你给我消停会儿!你以为我爱管你啊?就你这傻不拉几的样儿,昨晚被人下药,今天隔大街上乱窜,幸亏你昨晚上碰到的人是我,换个心眼儿坏的,你被人lun.奸了都没个准,现在社会多复杂你知道吗?”
↓↓↓后续内容点左下角抢先看!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