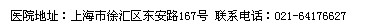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创伤性脑出血 > 脑出血病因 > 葬礼是一场表演,没有人看到你的内心在流血
葬礼是一场表演,没有人看到你的内心在流血
人人都有故事,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个故事
这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生活又该重新开始。母亲的葬礼
by张颖
母亲走的时候59岁,一场车祸,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老家的老人们说,59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母亲没能迈过去。那一天是年6月7日,我在异乡正为即将到两岁女儿的生日做着各种准备,却不知道母亲即将离我而去,而且是永久的离别。
那个夏天的早晨还是那么历历在目,六月的天气已经开始炎热,早上会有些许凉风,正是一夜睡眠即将结束,但却又是最深沉的时候,手机放在客厅,早起的第一件事,来到客厅拿起手机,却看到了十几个未接来电,是八叔,(其实只是我们的四叔,因为爸爸大家族的所有兄弟都按年龄排序,所以我们家的四叔成了八叔。)看着手机,心里隐隐的有些害怕,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否则,这样一个工作日的清晨,老家的父母和亲戚都不会打电话给我的。
盯着手机看了许久,才犹豫着把电话拨了回去,八叔的声音很平静,平静的感受不到任何情绪,他说,你妈出了点车祸,受了点伤,你回来看下吧。脑袋嗡的一声,半天我才问了一句,严重吗?八叔说,没事没事,一点小伤,你回来看看吧。没事没事。我“哦”了一声挂掉了电话。我知道他话里的矛盾,但却不敢多问,怕问出了我不想听到的答案。回了房间,老公也醒了,惺忪的问,什么事啊一大早的?我怔怔的说,我妈出车祸了,八叔让我们回去一趟。老公说,怎么是八叔打电话?我顿时吼了他一句,别问了,赶紧走。
一路往北开,路上老公假装轻松的聊天,我也有一句没一句的应答着,脑子乱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医院门口,却有一个从没见过的小伙过来说,是大姐吧,我带你过去,顾不上问他是谁,只想着应该是一个本家弟弟,医院的大门,我佯装镇定的问,哪儿?住院部?他支吾着。我说:“不是这是哪?他说,你跟我来。终于沿着那条路一直走,几乎走到了尽头,路边有一个花坛,花坛边坐满了人,二叔、八叔、八婶、六叔,十几个人全是我们家的人,为什么全是我们家的人?为什么他们全都抬着头看着我?我再也无法往前,一路上的所有的疑问都有了答案。
为什么是八叔打的电话?
因为我哥或者我爸那时已经崩溃,是不能给我打电话的。
为什么是一个我没见过的本家孩子来接我?
因为他跟我不熟悉,能控制他的情绪。
我双腿一软坐到了地上。只记得好多人冲过来,扶起我,拉着我往前走,我大叫着:我不去,我不去。最终他们还是把我搀到了那儿,妈妈平静的趟在那里,穿着像奶奶走时那样的衣服,这衣服叫寿衣。神态安详的没有任何表情。
只记得撕心裂肺的哭,想趴到妈妈身上,却有一个人过来拉着我说,不能这样啊丫头,不能这样啊丫头!这样不吉利,我知道老家有很多规矩,我知道我不懂这些规矩,我只想抱着妈妈,却又一次被拉开,在几次的挣扎中,我放弃了,蹲在地上继续哭,直到哭的天旋地转,我的颈椎,被我长时间的弯曲,又带起了我的头疼,仿佛要炸开的疼,却也无力抬起来。
太平间就是一件小屋,我坐在门口的花坛边,怔怔的望着小屋的门,妈妈就躺在里面,可是她不能和我说话,我永远失去她了,怎么会这样?不久前的两天,她还用我买回去的蛋糕机做了小蛋糕四处分享跟我打电话炫耀,怎么现在成了这样?
亲戚们不时过来看看我,八婶说,回家吧,看看你爸。我沉默着被亲戚拥上了车,到了家,爸爸不在客厅,客厅里全是人,我走进房间,爸爸背对着房门蜷缩着躺着床上,我走过去,叫了一声,爸,爸爸转过身来,满脸是泪,对我说,你妈没了!天榻了啊!是的,天榻了,能干的妈妈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和大小事务,爸爸乐得轻松,只管每个月上交工资,看看书、下下棋对家里的事情一概不问。
可是,现在,是的,天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本家的二老爹来了,二老爹是爷爷的堂弟,是我们宗族里很有名望的人,夫妻俩都是老教师,三个儿子都毕业于名牌大学,都在大城市里有着很好的工作和家庭,是本家人教育下一代的标杆。没有安慰、没有哭泣,北方的男人们不擅长这个,一个家族的老人更是不可能痛哭自己的晚辈,只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沉默。陆陆续续地,又有许多的人来,总是一声声的长叹,唉!这不是天掉的事儿吗?咋会有这样的事儿!
在老家,这也已经是个规矩,谁家有人去世了,在没办葬礼前的那几天,亲戚朋友都应该去丧家看看,安慰一下家属,虽然语言很贫乏、可能只是默默的坐一会就走,但是必须要去,也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丧家突然失去亲人的痛苦。每一个来的人都和爸爸坐一会,反复讯问着车祸的过程,于是爸爸一遍遍的讲述,每一次讲述我都心痛刺骨,甚至开始痛恨来的人,问什么要问,为什么每个人都要问,直到爸爸一遍一遍的讲述时,我的心比之前平静了,我逐渐明白,说出来,无偿不是一种缓解哀伤的方式。
知道我回来了,本家里的大妈、婶婶等女人们便陆陆续续的来看我,这也是一种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男人们去安慰男人、妇女们来安慰女人,这种安慰甚至于是一种煽情,刚刚结束痛苦的我不一会便会迎接来又一波客人,追忆、思念让我禁不住又开始流泪,这时,亲戚们便会说,丫头,别哭了有你哭的时候。
他们的意思我知道,在老家,亲人去世,绝不能这么默默的流泪,这么流泪离去的亲人是感受不到的,而是要嚎嚎大哭,并且要加上各种说辞,并且哭也要在正式办葬礼的那三天哭。这才是真正的哭丧。
丧礼上的嚎嚎大哭我从未有过,即使是母亲去世半年前外婆去世的时候,我也只是默默的流泪,却也没有按照家乡习俗哭丧,也正因为我是外孙女,也没有人在意。丧礼上真正的主角是女儿和儿媳们。我从未想过我现在要经历这一切,曾经想过,等到母亲百年的时候,还有几十年,那是这种旧有的风俗肯定已经改变,却没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快。对于年迈老人们来说,去世时总有儿女成群,哭丧的队伍声势浩大,而母亲,只有59岁,她只有一儿一女,和一些年轻的晚辈们。
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婶婶们搀着我,他们担心我承受不了。看着妈妈被推了进去,大火吞噬了她的身体,婶婶把我拖走,塞进了车里,我透过车窗看见那许多个烟囱里,有一个升起了白烟,我问舅舅,是这个吗?舅舅突然背过脸去,后背耸动着。
那一刻,不管过了多久,想起来依然让我窒息。
回到家,我开始披麻戴孝,本家的奶奶、婶子们开始专门找一个房间,负责做孝褂。一服孝是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做出的孝服必须反过来穿,叫做“毛朝外”。儿媳和女儿必须用麻绳扎在头上,头发披散。脚穿粗麻绳做成的鞋,走的时候只能拖着走。穿好便听见有人叫,快去迎啊!迎什么?我一头雾水,有人拉着我往外跑,迎面看见了哥哥抱着妈妈的骨灰走来,跪下去大哭,很快又有人把我拉起来说,好了好了,进去吧。妈妈的骨灰放在了客厅正中间。婶子过来说,丫头,你得去买花了,我不懂,他说让你叔开车陪你去买花吧,原来是买大的盆花,围绕在妈妈周围,这也是规矩。我哦一声就往外走,婶子一把拉住了我,把孝褂脱了,不然人家可不让你进。
我三十岁了,从十八岁高考离家,每年只有一小段时间待在老家,所以对老家的规矩知道的太少,因为从不需要我坐这些。花买了,六盆围绕着妈妈。这都是女儿该做的事。
一天的送汤开始了,送汤是老家的叫法,就是为去世的亲人送汤水。一天七次。所有的人都披麻戴孝,按照亲疏排序,送汤的路上会有许多人在路边围观,谁哭的厉害便是谁孝顺。而中药治疗白癜风方子白癜风医院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