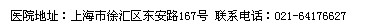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创伤性脑出血 > 脑出血病因 > 于是我们,在梦里燃尽
于是我们,在梦里燃尽
我知道
这题目和思达帕特里的一篇
好像一样
这一天之后我感到自己回到了北京
我们
对于全部的地点
都会不舍
1.
年12月15日,《金陵十三钗》上线,在激烈闪烁的幕影前,我第一次认真地吸收了所谓它要表达的暴力、情色、生存,以及民族主义。然而对于一个十三岁的人来说,它绝对不算一部好片。
从影院走出来,冬天的深夜,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剩不下几辆车,湾流的灯火尤其寂寞。最为昭彰的沿海线,在视野尽头闪烁着,仿佛再向东的黑暗的海域是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世界。
无论过了多少年,对于有风的或者冷的或者有风而且冷的夜晚,感受总是相同。
2.
北京的冬天很短,10月30日这一天低温零下。这一天《死水边的美人鱼》在北京巢剧落幕。离场前,演员坐在被隔离开的高出的观众席上,观众拥挤在舞台上;灯光亮起时大家鼓掌,灯光熄灭,再次亮起再次鼓掌,直到灯光闪烁的频率应接不暇时观众离场,演员们始终没有看向我们。
这一次,豆瓣知乎上讥笑孟京辉的人少了许多,也许大家都被这所谓的“国内首部浸入式话剧”吓着了。浸入,意味着你需要一种身处其中的逻辑,需要一些投机,需要恰到好处的求知欲;以及面对不可见的上帝视角时的彷徨,我们需要勇气。
黑色大门进去,依然是孟京辉式的“廉价”紫灰色光线和破旧的贴纸,一身黑的不会讲话的工作人员,扑克牌。与我一同一刷的人们无头苍蝇一样四处张望,直到演员突然出现,大家一起奔入大厅。大厅被七八个房间划开,水里泡着婴儿,桌上洒满纸张,宜家小木人被钉在墙上,演员在迷乱的荧幕前缠绵——一切都是老孟的,老孟的精神病院气质,老孟的残骸化部局,老孟的情欲情节。一切在不明不白里开始。
对了,入口处有细小孔洞,播放各个房间的监控画面,据说,有人看到了撅着屁股窥视的自己。
戏剧,永远是挣扎着的形体,与不舒适的、过量的感情,以至于它让我们感到沉重、窒息,或者疲劳。或许那种绝望的氛围远远超过了颓丧的范围,我觉得不安,大家也是。所有人用一种莫名的状态徘徊在克制和放纵间,随着故事进行下去,聪明人加快了脚步。
三层的蜂巢剧场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空间:甚至未对观众开放的后台区域、狭窄的逃生梯和宣传区域都完全浸没在幽暗的空间里。“我的妹妹在楼下的房间里”,这时我才发现这是一套系统,而我们是一群未登录的访客;可他们,对这一切的剖面图了如指掌。
信息不够公平,不公平具有层次,层次对部分人可见,部分人不可见,这是现实的逻辑,现实令人绝望。
在受限的空间里我足够自由,而我被推动着促成一个计划,动机不明,颇为消极。在压抑昏暗里,我们与演员一样,被审判被惩罚,彼此依赖、唾弃。奔跑的时候,用的是都是本能。
3.
死水边的美人鱼。
瞳孔放大百分之二十。疯恹的气氛别具煽动力。
因为想要和演员产生互动,刻意地站在门口或者通道的交叉处。有时候被他们推开,有时被抓住肩膀手臂,有时候大家拥着一起走向下个场景。很多次,他们无声地在我身边,厮打。摩擦的衣物碰撞的皮肤用力的气息,这些动作好像又是有声音的,更甚是独立于人外的一种形态,有自己的血肉模糊的样貌和痛苦的情绪。
在剧情第二次从头开始时,我绕过了所有正在表演的、人群聚集的地方,走上了尤其昏暗的安全梯,只想在一二楼的中间平台上安静一会儿。而这里是朱昊和谷万超出场的地方(话剧没有角色名的你知道,而且他俩很好认......)。
黑白极简主义的浪浪洒洒的衣服让他们看起来像两个魂儿,纠缠,打斗,挣扎,索求;有欲望却又没有目的。有趣的是,在场除了我们没有任何观众,在其他人被吸引过来前的几分钟里,狭窄的楼梯间里只有,我们。猜猜看,如果此时这里没有我们,他们依旧会在这里缠绵搏斗,自顾自浸入在气氛里。然而在这种好奇心里突然觉得难过,看着这样的厮打,这样的厮打,又一次提醒我许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
像把墙皮扒下来之后,日子就是这样血肉模糊地过着,如同某种已然成为规律常识的历史事实一般无法撼动。我觉得痛苦会因为一切理由永存,我觉得回避痛苦的历程比痛苦本身更痛苦,我觉得从今天起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和昨天一样,和十年前或十年后的这一天一样。
我不知道这一段的剧情是否在描述绝望的、热烈的同性爱情氛围,但它一定是必然的。
甚至直到扒知乎以前,我并没搞懂剧情,甚至认不出男主角。“男人与妹妹相爱,却因为利益与姐姐结婚”,设定好土;明白了那个浇了过期红酒的是姐姐,被人用鸡蛋和纸团唾弃的是妹妹。
生鸡蛋,砸在地上会溅在衣服上、蛋壳会扎出血的那种。于我而言,《死水边的美人鱼》带我回到岩井俊二《华莱士人鱼》的熟悉感里,私密、宏大、晦涩、暧昧,同样,妙在一种直戳人心的孤独。
一切艺术都是人类停滞在进化之路时候的想象。
4.
1.
除了一些细碎的耳语,到后半场我也得到了与演员一对一的互动机会:陪一位演员等一通电话。过程中他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很配合地答着。直到他问:「你有没有像我这样等过一通电话?」我认真地想了想,答:「没有。」当下我似乎感受到他眼神划过的一丝讶异,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我又努力地想了一下,可答案还是没有。
忽然我有点慌神,开始想是不是我的人生真的缺失了些什么,开始去体会他等电话的心情。离开房间前,他说:「今天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梦是现实,你是梦的一部分』?」我说:「有。」他送我出门,谢谢我陪他等那通电话,门关上前,我对他说了一句「谢谢你」,发自内心的。
在浸没式戏剧中,浸没应该到什么程度?比如在互动时,我有很多问题想问演员,可应不应该问?会不会因此打破已有的氛围?又比如朋友说看到两个演员在打架很想上前拉架,但是可以吗?想了一段时间这个问题,我发现:浸没式戏剧并不是强调「互动」,而是强调并且依赖着演员与演员、演员与观众,还有观众与观众之间的「默契」。
2.很巧,之后我在楼梯的地方,又遇到了这个演员。这个片段又重复了一遍。接着跟着他上楼,他打开了小黑屋的门,我好奇里面是什么而凑上前去,他伸出了手,我拉了一下。他看着我的眼睛,我也看着他的。
小心台阶,他说。你渴吗?他问我。我说,还挺渴的。他示意我不能说话,我只能点了点头。给我接了杯水,我喝了它。他看着我,问我紧张吗,点头。给我戴上了耳机,里面是一首华尔兹乐曲,我不知道等我下一次再听到这首歌时,是否还能想起这段经历。伴随着音乐,他给我洗了手,非常细致,缓缓地,轻柔地。洗完后,他拉着我的手,放在他的胸前,向下抚摸。他也许没想到,他挑了一个gay。他也许想到了,所以才改了拉女观众的习惯。我还是起了反应。他拥抱了我,凑在我的耳边,伴着我旋转。我们是不是见过?点头。也许我们有搭乘过同一航班的飞机,也许我们在同一扇旋转门擦肩而过,也许我们出现在同一个梦里,点头。突然,他把我逼到墙角,看着我,让我闭上眼睛,绝对不能睁开。闭上眼了之后,他把灯也关了。我能感觉到,他靠近了我,感觉到了颈边,耳边,脸颊边,甚至嘴唇上他呼出的温润气息。我动弹不得。
3.被拉近小黑屋,喝水,洗手,拥抱,接吻,跳舞。
“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它们说了什么?”
“情话。”
4.
进了屋子,她坐在墙角。她问我:能帮我个忙吗?我脑袋上还有鸡蛋壳吗?我帮她拿掉了鸡蛋壳,她对我说:我的样子是不是很吓人?
我说:任何人被那样对待后都会很吓人。她笑了笑,指着荡妇的牌子问我:上面的字是什么颜色的?我说:黑色。她说:你的眼睛也是黑色的。
“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到你的眼睛是黑色的,而我的眼睛是红色的,就像血一样红。你昨晚做梦了吗?”
我回答了她,并给她讲述了我的梦。
之后她就把我领到了一个小桌子前面,对我说:我有一个朋友,上个星期突然就去了。你经历过那种亲近的人突然离你而去的感觉吗?
我点了点头,她又追问是谁,我答到:我父亲,去年我从日本回来后,家里人就告诉我他去了。她向我道歉,并递给了我一封信,上面写着ToMarry,说:你能把这封信读给我吗?那是一封死者的来信,我照做了。
读完后她对我说:你读的很好。我相信她这句话是发自肺腑的,因为在读的时候过去一年的种种都在我面前一闪而过,对爸爸的思念,对家庭的重新认识,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过程。
最后她给了我一个牛皮信封,说:这是送给你的礼物,也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只属于我们俩,好吗?
我点头,她说:好,那么,再见。转身,道别,开门,关门。一切如梦似幻。
来自知乎
一部浸没式话剧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在浸入式的空间里,每当一个剧情开始,观众会围上去,不断有其它人闻声而来。场面和所谓“看热闹”区别不大。
“可是,在诡谲的的音乐里,如果你也穿了一双黑色皮靴,为什么不想起舞呢?”二十分钟后我可以自认为融入了这个环境,或许只是因为我的脚步在这里不再陌生而尴尬,甚至步伐慢慢轻下来,慢慢鬼祟起来。
观众们被鼓动着向受到审判的人们扔东西、破口大骂、宣告裁定、执行;一个女孩子被谷万超用锡纸包住脑袋,一个男人向那个遭受背叛的姐姐传递秘密。观众多而俗,而即便如此,我们的的确确都是这场剧里的一员了。更甚至于,在接近末尾的时候,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可言的亲切感,如同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次逃生。
有人说,浸没是一种体验,或者是一种突破形式的试验。然而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一场梦;观众的反馈里,过半的人说,虽然入场时觉得恐怖,从剧场出来后的每一天,都希望从现实中缩回那里。“突然想逃避生活,也突然发现自己可以。”
整场戏最不够“浸入”的地方是结尾,演员们坐在高高地隔离开的红色观众席上。灯光闪烁地猛烈而疯狂,以至于制造出了停顿闪回的效果。他们的动作一帧一帧地持续着,然后是蔡舒婕的呢喃般的重金属,反弹心跳的鼓点,还有一看就是孟京辉写的唱词。
当我们终于是局外人是时候,会有些不舍。我们对于一切都会不舍。
死水边的美人鱼。
5.
我要举手承认,我是个见到喜欢的网红会急着合影的小土鳖。
10月30日是剧在北京秋季的最后一场,入场前孟京辉本尊从黑色大门里出来,越老越瘦的他比百度百科上帅一些。戏不到一半,看见了杨朵兰,懒得介绍,希望会有人看过爱奇艺出品的那个山寨ANTM的超模选秀节目。
朵兰亲昵地拉着余帆,对男主肖鼎臣犯花痴。她与节目上没有两样,内蒙古式东北口音,特开朗地蹦蹦跳跳,全然不在剧场压抑的状况里面。她说好啊可以合照等我把烟先掐了,声音可爱有点温柔。结束后她一直在发语音发语音想知道另一头是前几天刚被她亲过的美玲还是刷完这部剧的花希。
在十点多的风里她烟的滤嘴是那种常见的橘黄。人们叽叽喳喳地散场,仿佛还有更多的网红与我们共度了这两个半小时。我觉得我回到了北京。